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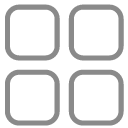
|
怀念端午粽叶香 文/单车 时光逝水,岁月如梭。自然无言四季流转,人生感慨寒暑轮回。2020年春节因为新冠病毒肆虐,城乡封闭,居家做囚,我们过了一个无限憋屈的春天。但时光抵不过季节交替,进入初夏,我们生活逐步恢复正常。我作为一名户外运动爱好着,也是趁着难得的好时光,在工作之余走进自然,享受大自然的恩馈。 农历四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我又向往常一样骑自行车到城北的八公山游玩。出北门时看到几位妇女在护城河边打苇叶,赤脚站在没膝的水中边攀摘苇叶,边叽叽咋咋的说话,不时传来阵阵的笑语。我当时没有多想,径直骑车了。在八公山里的闪家冲民族村休息的时候,回想起其北门外妇女打苇叶的情景,猛然想起他们打苇叶是包粽子,端午节到了。 端午粽飘香,小时候,每年的端午节看看左邻右舍,家家户户大门敞开,男人在扫庭院,洒雄黄,挂艾草;女人在炸油糕,包粽子,煮鸭蛋;儿童则穿新衣,佩香囊,缠彩丝,街头巷尾无不弥漫着节日的芬芳。刹那间,一股浓浓的端午情铺满我心扉,撩拨起我内心深处的痒。 端午节对我来说是一种难解的节日情怀,我对端午节可谓是又恨又爱。说起恨也仅是一点点,因为不自由不喜欢吃黏食,尤其是糯米做的粽子、年糕与元宵,反感这些食品的黏与甜。但我内心深处非常喜欢过端午节,甚至超过了春节,这种喜爱是我幼年最赋深情的记忆。这种记忆不同于春节时对美食与娇宠的期盼,也不是对寒假放松与自由的放纵,而是源于一种高傲与自满的幸福,及由此带来的自信、自足的滋生和漫延。 我幼年生活在寿县苏王公社苏王大队,俗称苏王坝。苏王坝的来由是源于流经村子的陡涧河,据说陡涧河河床低洼,农户不能利用天然水流灌溉农田,反而在夏季涨水时受其涝灾。苏王有苏、王二户人家行善举,出资修筑堤坝,兴利除弊,消除水旱灾患,农户感其恩泽,遂以苏王坝地名为之铭记。上述一切在我幼年的记忆里都与我无关,反而时常为我带来屈辱。因为我家是外来逃荒者,我爷爷那一辈从河南省逃荒至此,直至现在我们一家虽在苏王生根开花,延续发展,但在苏王本地人来说我们还是“老侉”,非其族类。 唯一让我骄傲与自信的是陡涧河里一望无际绵延十几里的芦苇。因为那是“我家的”!我爷爷是1937年12月日寇攻占南京时流落到安徽的,几经周折来到苏王坝(个中原因,我没有见过爷爷,他过世的早,我父亲流露过之言片语,但他不愿意多说)。我爷爷奶奶在村边陡涧河的荒滩上搭建窝棚,乞讨、帮工为生,直至解放。解放后,我父亲已经长大成年,就去江苏省找寻因抗日战争失散的亲眷,此去江苏虽没有找寻到亲眷,但我父亲发现江苏省湖泊水泽里生长的芦苇是很好的经济作物,在陡涧河的河滩上应该能够生长。我父亲就背了满满一麻袋芦苇根回到苏王,移栽在陡涧河的河滩上。头两年只是稀稀疏疏的出芽生长,但随后呈疯长趋势,我父亲栽种的整片荒滩全是芦苇,夏天碧绿,秋天金黄。端午前后,我奶奶依照江南的习俗,打苇叶包粽子,碧绿的粽叶,扑鼻的清香,玉糯的口感,只诱得周边四邻竞相学做。但最主要的芦苇长成砍伐后可以作为建筑材料,用来做房笆,春挡水夏防暑秋冬防寒,是农村可以换回现金的东西。于是陡涧河上下游的农户争着移栽,不到几年,沿河十几里地的河滩上长满了芦苇。直至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我家与其他农户家芦苇地一起被收归生产队公有。沿河十几里地的芦苇,大大改善了陡涧河的生态环境,引来许多不知名的水鸟,当时我与伙伴几个最爱当芦苇荡里掏呱呱鸡(一种不知名的水鸟,在芦苇荡里筑窝)的蛋,不经意的还能捉到甲鱼、乌龟,但那时我们都很少捉,因为没有人吃。这时节是我最骄傲的时候,我会指着大片芦苇趾高气扬的对同伴们吹嘘,芦苇原来都是我们家的,我的同伴们也曾听家里大人说过,个个点头称是。这时我回高扬着脑袋与同伴一起躲过看青(生产队安排看守芦苇荡的,大多为孤寡老人)的老头,钻入芦苇荡里玩耍,捉迷藏、摸鱼虾、掏鸟蛋。
我十岁上下的时候,就把端午节打苇叶的活独自揽下来了。我喜欢到芦苇荡深处听水流、听叶响、听鸟鸣,更喜欢青青苇叶被折下来的清脆与清香。那时节,看青的老头还装模作样的不让折苇叶,但知道人们对打苇叶包粽子的喜好,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曾经几次看到我抱着苇叶出来,还打趣骂道,小屁孩子,现在芦苇已经不是你家的了,我要让生产队扣你老子的公分。我听了心中更加满足,心里说,哦,这是我们家的苇子地!高高兴兴地抱着苇叶回家。 端午节正赶到午收夏种的双抢时节,农村收小麦、油菜,翻地插秧,连枷映月,水车响夜,日夜忙碌。这时候,我妈妈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村妇女,照例在忙碌田里农活,麦收芒种,天塌下来也不能放下手中活计,来不及为全家人包粽子。而我父亲虽然出生出生贫寒,但好歹读书识字,崇尚尊重民族传统风俗,在打理农活的同时,总是抽出时间包粽子,虽然因此多次受到我母亲的埋怨。他把我打回来的苇叶用开水烫后,放在清水中浸泡备用,再取适量的糯米淘洗后放在白瓷盆里加上清水,然后手把手叫我包粽子。他包的是榔头粽子,四四方方有棱有角,看着他折苇叶,放糯米,扎线绳,专心致志,简直是在加工一件艺术品,那种专注,那种娴熟,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忘记。 不仅如此,每逢端午将至,父亲总是提前打扫庭院,用马兰头水清洗门台及在门前喷洒雄黄酒等,有意无意的用自己的行动提醒母亲放下手中的活计,为我们准备端午的香囊、饭食等,母亲对没有忙完的农活虽有千般不舍,但大都会照顾父亲与我们的情绪,为全家过端午节操劳。母亲回从野外砍回艾草让父亲挂在大门两旁,用于驱邪;回从街上买回香草连夜为我们缝制香囊,寓意祛病;还会为我姐姐妹妹编栓五彩丝线手环,祈求吉祥。 端午节早晨,我们家的主食就是一大锅清香扑鼻的粽子,配置以全年很少见的红糖(白糖),而我从来不用粽子蘸糖,因为甜破坏了粽子的清香。我总是把粽子剥开,拿着苇叶细细的闻,感觉苇叶的自然香,然后把粽子放在口中一点一点满满的咀嚼,品味水的柔、风的轻、叶的韵。一个粽子足以!
时空变幻,沧海桑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外出求学离开苏王坝,以后落户寿县城关,我父母也因为年高,于九十年代中期搬到城关居住。至今离开苏王坝已经三十多年,唯独让我牵萦的就是那片苇子地。记得2000年以后,我曾经约了几个儿时的同伴回苏王找寻儿时的回忆,席间我提及去看苇子地。在苏王居住的玩伴阻止说,苇子地早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见钢筋混泥土楼房,不需要芦苇做房笆了,苇子地无人愿意接手管理,荒废已久。我不相信,乘着酒意独自一人去了河滩,找寻我幼年时梦。但现实将我击的粉碎,裸露的河滩上只有寥寥几株细如筷子,高不及一米的苇子随风零落。那片绵延十几里,又高又壮又密又绿的芦苇荡只能永远停留在我的梦里了,落寞黯然。 又见初夏苇叶扬,又闻端午粽飘香。那一片碧绿的芦苇荡,已经化作馨香的记忆,已经成为亲情的延续,已经融入我梦中的守候。年年端午,今又端阳;岁岁粽子,今又飘香;那一片芦苇,那一丝梦想。源源不断,飘飘荡荡。 |
|
Copy all rights reserved for www.hnpictures.com
淮南图片网 版权所有
地址:淮南市阳光国际城南区7号楼507室
备案号:皖ICP备15022074号-2
电话:13505548206、18949682288
邮箱:1147587489@qq.com
网站特聘律师:胡蓉
技术支持:淮南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