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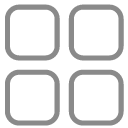
|
《百年一叹九龙岗》(二) 作者:天山 从民国十九年的秋天九龙岗掀起了通红的盖头算起,一眨眼,一百年过去了。我的故乡从一位豆蔻年华的少女成为了风烛残年的老媪。百年一瞬,百年一叹。作为一个九龙岗煤矿工人的儿子,没有能力从波澜壮阔的角度去描述九龙岗百年的辉煌与成就,也无法站在哲学的高度去探索九龙岗深邃的文化内涵,只能勉强的从柴米油盐,芸芸众生的角度,写点囿于个体生命和感情所限的小文章,发些小感叹,一次次眷念着九龙岗,倾听老街坊、邻里传来的乡音和岁月的味道。
这些年来,我曾去过陕西延安的黄陵煤矿,河南三门峡的义马煤矿,山西大同的云岗煤矿,内蒙鄂尔多斯的色联二矿……或许是太重的家乡情结影响了我的审美观,每到了一个地方,我总是习惯地用早已镌刻在脑海深处的九龙岗矿的格局和尺码,来衡量眼前矿区的布局,不是疑惑他们的审美观,就是对他们在荒郊野岭横七竖八的建矿布局感到诧异。我更加感叹九龙岗矿的工业广场布局竞是如此的熨贴,阔而不旷,精巧且合理。矿区的整体布置凸显了设计师与众不同,别具只眼的风格,周边的集市和生活区围绕着一个中心运转,从实际出发也从心理的角度,体现了家对矿的依赖,缩短了家与矿的距离,无论你走多远,走着走着,一眼看到了高高的“克虏伯”井架,就到家了。 民国二十年秋,随着九龙岗东西两矿相继投产,东矿的淮南村和西矿的南宿舍也同时开工建设。这两座住宅主要解决矿上高级职员和一般职员住家的问题。南宿舍坐落于舜耕山山下,东西长约二百米,南北宽约三百米,坐南朝北,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院内一条南北马路,将大院一分为二。沿马路东西两侧,分别建设一排排高级职员的宿舍,歇山式屋顶,灰砖黑瓦,木质的门窗,水泥地面,室内厨卫俱全。与南宿舍南围墙一路之隔,是一座砖石结构四合院,这就是原九龙岗矿职工疗养所。一九六五年,疗养所撤销,矿职子弟学校迁于此院。再往南便是舜耕山脚了。位于舜耕山以北,九龙岗矿以南的矿工们居住的地方取名“重华”,它的寓意很美,有封建王朝功德相继,累世升平的意思。重华村中间一条大沟把村子分出了沟东与沟西,中间盘桓着一个宽宽的坝子,坝上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路,路的南边种了一排又粗又高的柳树,北面则是一家生意兴隆的“王朝”小店。
九龙岗的露天大舞台原先在西矿东大门的右侧,是江湖上玩猴、要杂技、卖大力丸和秀肌肉的地方。也是孩童们最喜欢的地方。西小街的西南边有一座日式的悬空户籍室,行人从坡上走过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层小楼,而从北向南爬坡再看这座小楼,则是二层,里面铺满了木地板。南宿舍东南角的日本人建的炮楼还在,只是爬满了青藤。而矿东门南侧上坡道大水沟的桥边建有一座两层楼高的地堡,虎视眈眈的盯着过往的行人。 早些年的夏天,地堡下面的大沟的洪水退去之后,孩子们赤着脚常常会捡到黄澄澄的小铜块,到小贩子那里换糖吃,至今也不知道铜块到底是从哪里冲出来的。南宿舍的东面,祟文村的西北角,有一个名气很大的“窑神庙”,每年的腊月十八是祭奠“窑神”的日子,井下的包工头和矿工们都来祭窑神,以图得一年的平安。东矿电影院的西边有一个花园。花园里种植的都是叫不上名字的洋花。
一九三三年,国民政府在九龙岗设立了警察总署,建起了警务总所大院,即现在的淮南十四中所在地。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九龙岗百废待兴,淮南路矿职工子弟中学建立了,这所学校之所以命名为“淮南路矿职工子弟中学”,是因为铁路局在办校中的出资和担当都大于矿务局,因而确定把“路”字放在前面,校名一直沿用到淮南解放。学校创办初期曾二度迁址,一九四七年定位于公安村、新雅村后面公路边的一座旧小楼内(今天的淮南十四中)。十四中的西面是九龙岗第一小学(前身是淮南路矿子第小学)…… 人类大约从三岁以后开始有自我意识和记忆,所以,我的脑海中至今依旧贮存着五六年底的那一场大雪,飘飘洒洒的大雪中,一个穿着北方花大氅的小男孩在九龙岗西小街一座四合院外的雪地里和一群孩子玩耍的情景,从那时候起,幼年时的小脑袋便像小时候盛钱的“扑滿”,断断续续地装进了对这个世界朦胧的认识,再以后,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这个世界便清亮亮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了…… 那个时候的我在九龙岗二小上学,每天上完课之后,我像一只快乐的小燕子掠过九龙岗的大街小巷,记住了这里山的美、沐浴了父母的恩、邻里的情、老师的爱、同学的义。我在故乡念完了小学、初中、高中。从这里下放到了农村,再以后被煤矿招工去了本市的西部地区当了一名建井工人。九龙岗离我越来越远了,这一走竟然有三十年。
车子在斑驳的画中游,南门口外的店铺几经改造失去了原有的风貌,电影院、马戏场和公园拆除后,形成了如今的邮局和菜市场,原先通往大通和田家庵的公路也变成采煤塌陷水塘。在人流中已经找不到当年熟悉的通衢大道。下了车,步行到了十四中原先的大门前,通往校内的甬道还在,但门却是旁门了。大门正对面的邮电局已经作古,而北侧的日式建筑大病房也踪迹全无,学校爬满了青藤毛石砌的围墙还在,只是大门旁的白杨树仍在兀自疯长,越发显衬出母校门头的矮了。 再往东走,左拐,顺着新铺的村村通小路,找到了原先热闹的东九街。东九街的模样完全变了,十字路还在,但两侧的店铺已经全部坍塌。记忆中的饭店,米店,布店,拐头的药店,东头的澡堂子,卖山货的客栈都原汁原味还给了大自然。只有工商联的两层小楼还剩半边,孤零零地戳在那里,像是在诉说着昔日的辉煌。 原先的大街四面通衢,好不风光。现在竟空荡荡的,东南西北的木质大门早已毁坏,东九街滿目的残垣废墟在寒冷的冬天里裸露的一览无余……眼前的一切让我眩晕,诸如冬与春、昨与今、废与兴、毁灭与重生的字眼在我所站的东九街上空飞舞,仿佛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它们最合适的归宿......只有天上的云知道,东九街走了,像一百年前一样,空着两只手来,又空着两只手离去。竟不带走一丁点的东西…… 从南门口向北步行,穿过约一百多米绿荫掩映的天、地、玄、黄、宇、宙的老建筑,这座被人们称之为典型的民国小镇的代表,解放后被称为淮南村。“田”字型庭院布局,东西和南北两条道路将整个庭院划分为四组建筑,既独立成院,又相互依存,四周围墙形成了一个整体大院,成为当时安徽地区著名的庭院式建筑的典范。透过岁月的沧桑,依然还可以看出当年的大方得体的模样。
往北走,见到一座外观沧桑但不失古典风格的二层小楼,这就是淮南煤矿局办公楼旧址。典型的花园式建筑,曲经通幽,地势优越,中心凸出。大门紧闭,朝阳的山墙爬满了青青的爬墙虎,而朝西的一面,失去了生命的爬墙虎变成了一绺绺像掛在舞台上京剧老生下巴上的胡须,长长的稀稀的,似乎在默默地念白。 铁路俱乐部紧闭着大门,几十年前的水塔还在,曾经铁路所管辖的区域失去了往日的有序、整洁。曾几何时,淮南刚解放的时候,淮南铁路局从淮南煤矿局划分出来,最辉煌的时候曾经直管九龙岗地区的机务、车辆、客运三个段及电机厂,下辖田家庵、九龙岗、水家湖、合肥和裕溪口五座中心站,以及朱巷、下塘集、撮镇、巢县、沈家巷等20座车站。 车子往西转向南,曾经的林荫大道是西矿人上东九街步行最为凉荫的地方,两边的林子只剩下一片浸透着诗一般的朦胧和惆怅的水面。下车沿南宿舍东侧的路步行向上,左边的一条原本红火热闹的西九街不见了踪影,牵牛花在路旁散居民房的围墙栅栏上攀爬着,一路攀爬,一路开着小花。 我放轻脚步,举目向东山望去,半山坡竟被冬天少有的阳光普撒,一片灿烂金黄。沿着蜿蜒而略陡的山路向上爬,感觉地势与天的距离在逐渐的缩短,每上一段都缩短了许多。站在半山坡上朝西望去,重华村的所有建筑早已皈依了大地,再向北望去,一整片一整片因烧砖取土和房屋拆迁而形成的洼地和残桓废墟似乎告诉人们,这才是一百年之前的模样。
红红火火的九龙岗,一半皈依了盘着九条龙的大地,而另一半则顺着时代的潮流注入了今世的俗媚。面对西矿和重华村的方向,竟找不到了童年时曾经玩耍过的地方……… 每当我行走在闳约深美的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和风光旖旎的外滩,看到眼前被美轮美奂的灯光幻化得淋漓尽致的精美建筑时候,早些年,蒸汽机车疲惫的拉着整列的煤炭呼啸着向上海奔来、以及故乡的井下采煤工挥汗如雨的镜头总是交织在眼前!虽然脑海里浮现出来的东西和眼前的人间仙境是相互不搭嘎的概念,虽然这一相互联系起来的镜头,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已经仿佛通过公平的价值交换的方式给予了解释,我的眼前仍然浮现出六七十年代,上海市政府为了感谢淮南矿务局对上海经济发展的支持,曾数次组团来家乡慰问的场面。现如今,这种热闹的场面被没有羼入一丝丝感情色彩的商品交换的方式来替代,似乎在告诉人们,上海今天的兀立和繁荣与眼下家乡的坍塌和废墟在价值交换面前竟然是如此的彼此安好,两相情愿?
曾经年产七十五万吨优质动力煤的九龙岗矿,从民国十九年开始到公元一九八二年整体搬迁,五十多年的担当和贡献(史料记载从1930-1982年计52年,共生产了煤炭2457.8万吨,其中,从1949年至1981年的32年间,九龙岗矿共计生产原煤2020.6万吨,是1930年至1948年间出煤的4.62倍)。曾经热火朝天的九龙岗,一骑绝尘的九龙岗,负重爬坡般的走过了百年的路程,它的离去,它的厚重,足以让今天的上海人对它注目。 家乡的残垣和废墟,在别人眼里是视觉上的荒凉和破败,但对于从九龙岗长大的人来说,却把这种坍塌和废墟看作是传说中的九条龙拔离了大地,完成了泽润一方黎民百姓之后的皈依。眼前的一切似乎还告诉了人们:凡是有资源的地方,它的辉煌和结局概莫如此!如何解除这令人叹惋的咒魔,是百年九龙岗人乃至淮南人的梦想与期盼。
(淮南图片网大通区分站特约稿) |
|
Copy all rights reserved for www.hnpictures.com
淮南图片网 版权所有
地址:淮南市阳光国际城南区7号楼507室
备案号:皖ICP备15022074号-2
电话:13505548206、18949682288
邮箱:1147587489@qq.com
网站特聘律师:胡蓉
技术支持:淮南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