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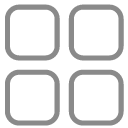
|
今天的课比较少,下了课,按照惯例,我从学校直接去看望现在一人独居在家的母亲。 初夏的天空瓦蓝瓦蓝,远处的八公山换上了碧绿的衣裳。路两旁的香樟树枝繁叶茂,微微暖风催得田野里的各种鲜花格外地娇艳,红的、紫的、粉的、黄的,像是绣在一块绿色大地毯上的绚丽斑点。蜜蜂在花丛中忙碌着,空气中到处氤氲着花的香味。忽然一簇小花吸引了我,百合一样的花朵形状,橘黄色的花朵,橙色的芯,翠绿的梗,挨挨挤挤地,在微风中摇曳着明媚的黄。用“识花君”识别了一下,是萱草。我马上就想到了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萱草花》:“遥遥的天之涯萱草花开放,每一朵可是我牵挂的模样,让它开遍我等着你回家的路上,好像我从不曾离开你的身旁。”没想到这不显眼的花儿,居然就是萱草花。 萱草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诗经﹒卫风﹒伯兮》载: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谖草就是萱草,谖是忘的意思,故萱草又名忘忧草;背,北,指母亲住的北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到哪里弄到一支萱草,种在母亲堂前,让母亲乐而忘忧呢?由此母亲住的屋子被后世称作萱堂,以萱草代替母爱。如唐朝孟郊《游子诗》:“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倚堂门,不见萱草花。”宋朝叶梦得 《再任后遣模归按视石林》:“白发萱堂上,孩儿更共怀。”元代王冕《偶书》:“今朝风日好,堂前萱草花。持杯为母寿,所喜无喧哗。”因而萱草就成了母亲的代称,萱草也就自然成了中国的“母亲花”。
萱草花 我母亲姓刘,在她姐弟5人中排行老大,娘家是山王镇山刘家。我小时候母亲经常跟我讲她爷爷(我太姥爷)、她父亲(我姥爷)的往事。我姥爷兄妹6人,他是老五。我姥爷小时候家境很好,兄妹几人都上过私塾。我姥爷打得一手好算盘,我小时候还记得姥爷一直是大队的会计。 我母亲跟我说过太姥爷家的破败跟日本鬼子攻打寿县从凤台县路过他们那儿有关。我查了一下史料,日军曾于1938年6月4日、1939年11月5日和1940年 4月12日三次占领寿县城,第二次攻占寿县时路过山刘家。1939年11月4日,驻守田家庵的日军沿着淮河溯流而上占领凤台县城后,兵分两路准备攻占寿县,一部分继续溯流而上,一部分从陆路走近道。得知日本鬼子要经过,沿路的各村庄的老百姓纷纷“跑反”,躲到山上,躲到树林里。山刘家的人也纷纷躲了起来,日军在向导的带领下走的是山路,结果把躲到山里的村里人全部堵到山坳里。日军抓住村里人后,由于要急着赶往寿县,只找了村里的大户索要钱财,太姥爷也是其中一个。谁心甘情愿地想把辛辛苦苦攒的钱财拿出去呢?日军用老粗布把太姥爷裹住,蘸上桐油活活给烧死了,家里人最后只好把钱财拿了出去。从那后,太姥爷家就破败下来,到我姥爷成家时,家里已经入不敷出了。我母亲生于1945年,小时候只读过几年的书,从二年级上的,一年级的拼音一点儿都不会。母亲对不会拼音始终耿耿于怀。到了三四年级的时候稍微大一些了,姥爷把我母亲和大舅喊过去,问他们是想吃饭,还是想读书。因为跟着生产队干活可以挣工分,所以我母亲和大舅一起辍学干活了。 我母亲七八岁时下巴下面长了疮,姥爷他们忙着生活一开始没重视,直到浓水顺着脖颈洇到胸脯上,他们才开始着急。带着母亲四处求医,找土方子,一直无效。看到母亲痛苦的样子,姥爷他们甚至想过到凤台县赶集过淮河时从船上把母亲推下河,一了百了。吉人自有天相,姥爷带着母亲从凤台县赶集回来在老孔集那儿遇到一个人,看到母亲的样子,一下子指出症状,告诉姥爷一个偏方。果然,偏方保住了母亲的命,疮渐渐好了,母亲的胸脯上落下了结痂的疤痕。由于脖颈下巴的皮都溃烂了,最后到医院从后背上揭的皮补在脖颈的位置,但下巴那儿的脖子始终仰不起来。 母亲21岁时嫁给我父亲的。父亲比母亲大7岁,又是残疾人。我很多次都问母亲当初看上父亲哪一点。父亲虽是残疾人,但父亲天生不显老相;虽然穷,但吃苦能干,又是城市户口,这在当时足以吸引一个农村的女孩了。父亲母亲打过结婚证后,没有酒席,母亲提着包袱就进了段家的门。我们家最初在沈巷孜住,后来有了我哥、我姐和我后,房子住不下了,就在煤建公司靠近水张铁路的东边一片空地上盖了两间门朝南的草房,拉起了一个院子,院墙是草坯垛起来的。我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长大的。 小时候最喜欢听母亲给我们讲她小时候从姥爷那儿听的“赵匡胤困南塘”“刘金定大救驾”“吕蒙正寒窑”的故事了。吕蒙正的故事现在还记忆犹新。吕蒙正是一个孤儿,小时候要饭,穷困潦倒,自嘲自己:“我身睡青灰头枕瓢,天上的鹅毛往下飘,我吕蒙正得了安身处,天下的穷人怎么得了?”吕蒙正有个叔叔,过年时杀了猪上街卖猪肉,吕蒙正去叔叔家,婶婶看他可怜,把留在家里的猪头给了他。叔叔回来后,责怪婶婶,让她把猪头要回来。婶婶无奈只有照办。吕蒙正说道:“可怜可怜真可怜,猪头烀熟又归还。我吕蒙正从今以后不得第,一笔勾销永不提。从今以后若得第,一年要过两个年,正月十五是大年。”吕蒙正发愤读书,81岁得第。还有《十五贯》的故事,到现在还能记得。
吕蒙正《寒窑赋》 小时候我的下巴长了“羊胡子疮”,羊胡子疮是男性胡须部位毛囊及其周围由病菌感染引起的一种皮肤病。民间疗法把公羊的胡子烧成灰,用麻油调匀涂患处。小时候我的手有冻疮,偏方是把旧棉花(越陈越好)烧成灰,用麻油调匀涂患处。记得那时候母亲经常到处找公羊胡子,到处找旧棉花。我现在的下巴和左手无名指上还留有疤痕。 小时候,家里很穷。一家六口人,只有父亲在职工理发店(属于新庄孜多种经营一公司,大集体性质)上班,父亲又是残疾,腿跛站着理发不出活,经常还生病,挣的工资微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们兄妹四人也很早就开始为父母分担生活,拾过菜叶,捡过破烂,打过零工。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母亲把我们从附近煤场扫来积聚起来的煤渣打成“炭饼”用来烧锅做饭的情景;记得母亲用姥姥家给的麦秸秆和秫秸秆编织稿荐和床笆用来做床垫的情景;记得母亲把我们从菜市场拾拣来的西瓜皮,削掉别人啃的红瓤和最外面的瓜皮后挂在铁丝上用来晒成干菜的情景。随着我们的渐渐长大,家里的花销越来越多,1982年父亲四处求人,在一公司为母亲找了一份在绣花厂烧锅炉的工作。1988年父亲又四处求人,把母亲的小集体工种转成了大集体工种,调到八号井上班,甩炭泥、编笆子、扛“铁猴子”。记得那次求人办事花了400块钱,那时对于我们家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稿荐 家里生活实在太难了,作为老大的我哥初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姐姐高考失利后也就参加了工作。相对他们,我算是幸运的,1989年高考考上了淮南师专。俗话说:“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教师是清贫的,但师范类学校的费用不高,可是最初开学报到的费用263元却难住了父母,不过最终家里还是想办法筹到了钱,让我顺利地入了学,三年后我毕业分配到中学教书,家里的日子才渐渐好起来。 1993年,母亲随父亲一起退了休,我们兄妹也渐渐到了嫁娶的年龄。母亲开始操持着哥哥于当年成了家,接着姐姐、我、我弟也陆陆续续先后成了家。母亲尽心尽力地服侍着父亲,每天早晨用轮椅车推着他出门锻炼,让他尽可能地也活动活动。我们兄妹几人没有了后顾之忧,各自忙着自己的小家庭,工作之余带着孩子去看望父母,父母也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由于长期生活的压力和劳累,母亲2009年罹患直肠癌,好在发现及时,是早期,手术也非常成功。2018年4月又因患肠梗阻做了手术。而父亲从2015年起,身体明显地一日不如一日了。父亲虽然腿跛,但年轻时不拄拐杖,退休后渐渐地拄起了单拐、双拐,直到依靠轮椅车代步。2017年时已患了轻微的脑梗,2018年上半年病情急剧加重,不断地住院、出院、再住院,一直到10月6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2019年11月,母亲居住的棚户区进行第3次搬迁。为了避免母亲触景生情,这次我们兄妹硬说服母亲买了一个小套的新居,于第二年10月12日搬离了居住了47年的老宅,来到了新小区。母亲也渐渐地从原来的悲痛中走了出来,渐渐适应了新环境,现在生活非常有规律。我们兄妹几人谁有时间,下班就去看看母亲陪她聊聊天,或是打电话陪她叙叙话。 五月是一个万物烂漫生长的季节,一进入五月,“母亲节”,一个无比温馨的主题也渐渐走来,这是一个从西方舶来的节日。与之配套的,是西方的母亲花——康乃馨。殊不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的泱泱文明古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自己的“母亲花”——萱草。萱草花,朴实无华,不张扬,不造作,生命力顽强,就像中国母亲对儿女的爱,含蓄而热烈,深沉而久远,蕴藉而醇厚。 五月萱草香,五月情意重。当记忆之帆穿越岁月的光阴一路驶来,满载的尽是母亲沉甸甸的关爱和希望。萱草葳蕤,从丛丛翠绿到明媚的摇曳着的黄色,再到步履蹒跚倚门眺望的身影,我们是要该常回家看看。萱草一岁一枯荣,爱我们的人也在慢慢变老,老得没有了别的追求,就只剩下喜欢见到我们了。今天在去看望母亲的路上既然看到了萱草花,那么,我就掬一捧萱草花,去送给母亲吧。
萱草花
作者简介: 段昌富,文学学士,民建会员,中学教师。2015年在《光明日报》与民政部主办的“寻找最美地名”征文中获三等奖;2016年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办的“追寻红色记忆”征文中获二等奖;2020年在《农民日报》与农业农村部主办的“我心中的美丽村庄”征文中获三等奖。现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淮南市作家协会理事、淮南市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八公山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八公山文学》执行主编。 |
|
Copy all rights reserved for www.hnpictures.com
淮南图片网 版权所有
地址:淮南市阳光国际城南区7号楼507室
备案号:皖ICP备15022074号-2
电话:13505548206、18949682288
邮箱:1147587489@qq.com
网站特聘律师:胡蓉
技术支持:淮南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