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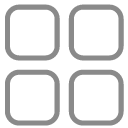
|
老井,真名张克良,是煤矿井下工人,业余时间喜爱创作,在各级文学刊物如《诗刊》《星星诗刊》《扬子江诗刊》《诗歌月刊》《阳关》《杂文选刊》《阳光》《中国煤炭文艺》《诗神》《青年月刊》《中国铁路文艺》《安徽青年报》《美国新大陆诗刊》《新诗》《西部作家》《牡丹》《剑南文学》《荒原》《巫山》《湖南诗人》山东诗人发过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篇作品。有诗入选《中国2010年度诗歌精选》、《中国当代新诗三百家》、《中国红色诗歌选》等。组诗“煤雕”获得有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国煤矿文联联合颁发的第五届全国煤炭文学“乌金奖”。组诗“岁月的醇酒”获第六届“华夏情”中国诗歌散文邀请赛一等奖。作品是中国煤矿文联、安徽省散文协及淮南市作协会员。被江山文学网江南烟雨社团邀请为特邀顾问。 诗观:呈现、悲悯、忧患、厚重,底层写作,深度叙述,草根性写作,原生态写作。
第一辑 深处写作 煤火 他正在井下干活 2001年1月 (刊于2003年第11期阳光,获第五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 廉租房 2011皖中大旱 禾苗和辣椒伏在田野里不动 市场上的物价和 股市荧屏内的绿色植物飞速上涨 乡野上一缕枯瘦的炊烟,搓着干瘪的麦穗 城市里,两个恋爱的男女 准备以三百年的工资做抵押 去订购精致的巢穴,大旱大旱 阳光无边、阴凉不见 房价房价一路上扬.高耸入云 我女友美丽的脸在一夜间变成荒原 我父母湿润的笑容里,掺上水银和黄连 大地上滚动着大团的燥热与无奈 我还是躲到清凉的井下去吧 穿着窑衣、拿起铁镐 井底刨食、地心修炼 一心只采眼前煤 两耳不闻地面事,假如遇到敢砸到我 敢掩埋我的那堆矸石 那就说明我下辈子的廉租房 有了着落 2009年10月 (刊发于《诗刊》2013年11月号下半月刊) 化蝶 干完了一般的活 坐在巷底的铁轨上,等待交接班 邱六说:“我猜今天地面上, 一定是个晴空万里的日子。 晴朗的晴、 空荡的空、 万恶的恶 , 里海的里。”二毛说: “地面一定是个大雨瓢泼的日子, 弟兄们上井就一定能看得到, 邱六的老婆正穿条花裙子站在、 碉堡一样厚的乌云里, 端着巨大的水瓢往下泼。” “一个两个的不是想上窑、 就是想别人老婆,也就这么大的出息了! 告诉你们,哥哥我现在只想 和本矿电视站的播音员柳淮丽、 同时变成两只彩蝶, 相互追逐着跃入到乌黑的煤壁 再也不出来。等到后来人开采!” 说这话的是满脸稚气的青工江小帆 2009年10月 (刊发于《诗刊》2013年11月号下半月刊) 坐井观天 淮北平原上煤矿很多 落日沿着那座井筒调零至地心 月亮又是扒着那座井架爬上来 我实在是统计不出来 每日在地心深处劳作 我只是凭着不远处井筒的战栗 就察觉到了黑夜和白天的交替 春天里煤壁花瓣一样柔软清香 冬季时瓦斯马峰一样在工作面上乱窜 夏天里整片巷道变得像一条湿漉漉的蟒蛇 秋天时成熟的煤炭豆荚一样炸裂开 在地心深处坐井观天的我 像一个久经沧桑的老农 通过阅读煤炭这部旷世的大书 就能感应到踩着自己头颅走远的季节脚步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某日我轻轻地吟出以上的句子时 连一直扳着面孔的地心岩层中间 也有了细小的动静 像是有谁正从中间爬起来 2009年10月 (刊发于《诗刊》2013年11月号下半月刊) 地心的戍卒 打眼、放炮、出矸石 只要一下井便是如此,时间一长 便觉得我们的躯体和周围的 凿岩机、风镐、矿车有些相似 敲打一下自己咚咚作响的胸膛 工友们指指旁边的物件说: 我们还是开口拉呱吧,再不发言 大家真的变成了它。出矸石、和泥 搬瓦石、砌墙······。粗粗算来,几个月来 我们已经用了上千吨的水泥和瓦石 不知不觉中巷道已经前进了三百多米 三百多米在万里长城也算是短短的一段吧 这么说我们筑的是地心的长城 在下就算是当代的万喜良吧 但草原铁骑何在?边关戍卒何在 狼烟烽火何在?说这话时我们的脸上 都镀上一层发绿的铜锈,有的人恨不得插翅 飞上地面,去会见自己的孟姜女 有的人把躯体直往巷道里挤 仿佛真要当那万里长城中最柔软的一段 2009年10月 (刊发于《诗刊》2013年11月号下半月刊) 壮志未酬 乌黑的精煤,挤压在煤场内 这么多凝固火焰缩成危险的一团 它们怀着燃烧的念头 在小小的空间内耗费着苍穹的寂寥 在一种怀才不遇的委屈中,久久等待 寒冷的风从它们的肌肤角层 剥下意志的碎片和虎豹的嘶鸣 但寒冷的风却吹不进它们的内心 吹不灭那一团包裹万里山河的神火 在天仓,在地仓,在工业食粮的囤积地 我闻见了一种壮志未酬的焦灼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这一群肤色油亮的黑马 梦寐腾开火焰的四蹄,煤堆表面冒起的青烟 画出几十个朝代膜拜的图腾 几只水枪从高处喷射过来,远海的冷静与湿润 击中我心中愈来愈热的燃烧念头 此时忽听汽笛响起 一列火车和几辆汽车念着打开心锁的密码 同时开来 2012年5月 晚开的蟠桃 牵牛花挪开大平原的寂静往篱笆上爬 一只毛绒绒的小鸡啄破季节温热的蛋壳 鲜嫩的鸣叫桐油般地涂满 我心底的柴扉上 谁在轻轻地叩门,我卷开眼中的草帘 却发现赶回娘家的老邻居翠珍,走错了房门 她丰芙的身躯里揣满了理想的积淀 行走起来已不再轻盈如兔 我一阵慌乱,她一阵尴尬,户外的田野上 有几朵晚开的蟠桃花,正用粉红的小嘴啄破了春天 “啪”“啪”的巨响,像是有几只 点燃的鞭炮被扔在了,我们心房的大门前边 还有许多的桃花被我一一错过 还有许多埋在地心的积淀需要我去开采 在煤矿井下刨煤时 感觉内心淤积的花香已高过,脑中冰冷的雪线以上 我遍体上下,淌出许多乌云一样地绵软的虚汗 2012年5月 (获第六届“华夏情”中国诗歌散文邀请赛一等奖。) 地心的浪漫 煤层松软一些,瓦斯的含量就会大一点 如此多的亘古动植物灵魂,争先恐后地往外涌 肯定会携带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煤尘、比如说焦灼、比如说岔怒 没有谁的灵魂可以帮助呼吸 在地心狭小的巷道里劳作 我们只感到被一种沧桑和悲怆压低海拔 当动植物们的灵魂多一片在体内悸动之时 我们就会脱去一层外衣 没过多久,男人们的身上仅剩下一片树叶 “我是否需要捡起一根杂木棒, 去抵挡煤体内猝醒的虎豹。 我是否需要捡起一块石灰岩, 去敲打炭堆内迸出的坚果。”停工的时候 一个诗人的浪漫就以一朵桃花的卓约身态 就在这乌黑,蛮荒的矿洞内通红地膨胀开 2012年5月 检修时间 几个工蚁般的男人,在深邃的井筒里忙碌 清理罐道检查钢丝绳 身挂着长长的保险带的他们 如同捆绑严实的粽子 被时光的火焰蒸煮,从地心的最深处 这黑暗的锅底一点一点地往上浮 开始抬头只能看见井口大的蓝天 慢慢地检修到了地平线以上 目光已经和井口的工业广场一样宽 最后终于爬到了井架的顶端,环顾四野 已经可以用目光中柔软的柳烟 去打捞百里平原尽头,那团正游动在静湖底部 啃食水草的青翠民谣 2012年5月 嘘!轻点声 几块人形的大炭,靠在黄昏干瘪的墙角 打开肌肤表面遍布的雷达 捕捉冬天阳光温暖的信息,一滴一滴地 挤出体内滞留的寒冷与黑暗 “那么白的墙平,那样黑的人体。” 几位清洁工嘀咕着,垂下眼帘里发育丰满的冰川 用比黃昏还暗淡的表情 打扫着井口宽敞工业广场里的喧嚣 仿佛这几块沾满煤灰的身躯,就是 点开了黑夜下载软件的无线鼠标 ……嘘!轻点声,不要惊吓他们体内 刚刚纠集起的新春暖意,不要惊散他们口中 刚刚升起的、青烟做的幸福 不要惊动那高耸的井架 它正伸长臂膀,径直地握住着自由替换的天象 要让那仍有些许暖意的夕光 多从这几个光热贫瘠的躯体内 兑换出一些沉重和疲惫 2003年7月 (刊于2009年第四期中国铁路文艺) 落日砸响井架 落日从长空中坠下,砸响了高耸的井架 “砰”的一声巨响传出 天地止不住地打着踉跄 落日收到了严重的内伤 霞光像它的剧痛它的鲜血 满天的挥霍 、一地的尖叫 钢铁的井架在抵挡住了 来自苍穹中的无边敌意以后 也像个头顶挨了一闷棍的男人,只是沉重的一哼 便从五脏六腑中喷出了岁月的黑血 这滚滚不息的煤潮呀 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决斗 傍晚,恰好从这场不共戴天的血战中穿过 我发现:夕阳战死、井架重伤 只感到头顶的威赫与荣耀 一寸寸暗淡。苍穹一寸寸地升高 脚下的坚实与存在 一点点松软。大地一点点地陷落 2004年10月 (刊于2009年第四期中国铁路文艺) 瓦斯爆炸 砰的一声巨响,大地晃了晃 1999年初春 在矿业集团安全培训中心 老师拿出加厚的玻璃试管 把一头用厚布塞紧,另一头接到机器上 充入瓦斯、空气,再电动打火 砰的一声巨响,那束毒焰舔破瓶塞 扬长而去,在辽阔的天地间很快没了身影 矿工学员们拍手叫好 他们脸上的绿色 没有烧焦,眼底的树木也没起火 再炸一次吧,老师 众人皆为自己能现场目睹瓦斯爆炸 仍皮毛不损,而欢呼雀跃 再炸一百次,一千次吧 我生在角落里悄悄换算着 地表到地心的距离 ——梦想把地心深处的所有爆炸 都搬运到玻璃试管中进行 梦想辽阔的地心 一直哑寂 狭小的试管内一直炸着 1999年4月 (刊于2009年第四期中国铁路文艺) 海离开这里多久了 地心的巷道一点点地收缩 从采空区吹过来的风 冰凉,咸腥,还夹带着亘古游鱼冰凉的叹息 海到底离开这里多久了 望着岩层上鱼鳞一样斑驳的花纹 我有时也会想一下这样的问题 亘古的浩瀚海洋 已缩成清泉般大小的一团 从岩罅间膨胀开,那少女般舞动的瑰丽目光 牵扯着黑暗的发丝地向低洼处流淌 它是煤块的情人,还是岩层的眷恋 清凉的注视挂在巷道里的钢梁铁柱上 地心的气温陡降了数十度 白帆何在?水手何在 岁月的船只抛锚之处 炙热的煤壁全都沉吟不语 我从手捧的炭块中找到了 一片草履虫的爬行痕迹 2010年12月 (刊于2012年第12期阳光) 钢铁的丛林 钢铁的树木一米一米地将地心的空间撑大 躯体坚硬 浑圆 缺少叉枝 通体上下不见一片绿叶 一接近它就能听见其体内 热血滚开的声音 可以随时长高 也可立刻变矮 宛如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 撑起了地心安全的蓝天 在钢铁的丛林中行走 我可以听见头顶不远处阵阵闷雷 看到从死神黑洞洞枪口内射出的弹丸 被挡在两三米开外 钢铁的丛林 依靠液压的力量 一点一点把地心下陷的天空撑住并拔高 每一片丛林下都站着或跪着 一个漆黑的矿工 打眼 装炸药 攉炭 地心的丛林深邃 蛮荒 在其中穿行 当我们站着时就顶到了苍穹 当我们跪着时就接上了地气 钢铁的树木站的笔直 躯体坚硬 浑圆 通体上下不见一丝绿 像我们的骨架和意志离开肉体突兀地站立 当一阵清凉的微风斜过地心之时 我却听见它们梦里萌发的绿叶 哗哗地掀动着地心无边的黑暗 每一片的绿色的裙裾都可能承载着 一吨矿工灵魂里的春意 2010年12月 (刊于2012年第12期阳光) 停电事故 突然停电 ,通风机才停转几十秒钟 瓦斯检测仪中,沼气危险的脸已经清晰可见 检查员和班长的争论还在继续 要钱还是要命的千古话题 也被煤体和周围的机器次次提起 直至从矿调度电话听筒里,跑出一头狮子的怒吼 把掘进工作面推搡得地震般晃了几晃 大家才绵羊一般慌张地离开 工作面瓦斯超限,再也不用干活了 愁眉苦脸的领导愁成了苦瓜 工人们却像装满蜜罐的陶器 脸上冰冷,内心鲜甜。一班人都睡得婴儿般宁静 安详。我睁眼就看到周围的黑暗手推车般 吱呀吱呀地,碾过来压过去的 这么多浓得化不开的好墨 一生一世都用不完啊,打开矿灯 又发现圆筒状的巷道像大地的一截小肠 裹住我们这几截无法消化的絮物 缓缓地向时空的尽头蠕动 2010年12月 (刊于2012年第12期阳光) 蘸火 上行的大罐开的越来越快 矿工们已经开始摇晃 每个人的头顶都冒着生命的信息 宛如钢铁的体内悬挂的 几副温热的内脏 大罐匝开周围的长夜 眼前溅起层层的黑浪 一层层波澜壮阔地翻滚着 大的像山脉 小的如绵羊 炙热的铁 升到冬天寒冷的地平线之上时 乘客们的滚烫的躯体中 会响起一阵“嗤 嗤”的声音 每个人的躯体表面还可能冒起一阵 灵魂一样轻盈的白眼 宛如一把烧得通红的钢刀 被放在冰凉的清水中 一点一点地冷却 2010年12月 (刊于2012年第12期阳光) 断电 综掘机轰轰隆隆地开动 丧失了疼痛感的煤体如田间炸裂的黑豆 哗啦啦地躺下长长的工作面 矿灯晃动 人影匆忙 我从空气中纷飞的粉尘中 闻见了处女煤的芳香 ——亿万年前油松的气息 石炭纪落叶的味道 “凝固的火焰 绵恒的史诗。” 我用粉笔,在机器钢铁的外壳上写下 这么一句话,然后擦去 地心深处,有一条蜿蜒的万里长城 晃了晃它黑龙般的身躯立刻恢复沉睡 沉重的综掘机忽然急停一下 又重新开动 像是它的体内忽然断电,又立刻恢复 2010年12月 (刊于2012年第12期阳光) 掉顶事故 干了一班的活,身体实在疲惫的难受 上下眼皮内如同按装着 两块异性的强力磁铁 还在拼命支撑 用铁镐小鸡啄米般地叨着 早已丧失疼痛感的煤层,但在某一时段 上下眼皮还是被短暂地粘在了一起 片刻 ,一块蓄谋已久的黑矸石 乘机从巷顶上冲下 ······铁镐落地 砸在巷底钢轨上产生的金属颤音 像两只柔软的手指 塞进我的耳孔中,直到几个月过去 我胳膊上的石膏,拆掉以后才抽出来······ 此后,我光洁的肌肤上 便留下了一段青灰色的疤痕 像是天空用闪电的锯条 锯出的痕迹 2010年12月 (刊于2012年第12期阳光) 在小煤井上夜班 开始是直着身子干得 上下纷飞的镐头,像是虎豹的巨齿 凶狠地啃下片片黑肉 随之就得佝偻着躯体干了 左右盘旋的镐头,小鸡啄米般地叨着 大地热气腾腾的内脏 前方的巷道越来越矮 最后不得不俯下身去,当他的双膝 重重跪下之时,头顶掉下了许多碎煤 时光一秒一秒过去 瞌睡一阵阵地从脚底往上爬 他的动作一点点地放慢,快到下班时间时 那深深地扎进煤体内的镐头 再也无力拔出 远远望去,多像一只温度表 在量着大地的体温 2008年9月 (刊发于2010年第4期《扬子江诗刊》、入选中国2010年诗歌精选) 看不见的春天 天不亮骑车去五十里以外的 煤矿下井,繁星满天时下班回家 路过一片庄稼地 浓稠的油菜花香,蚕豆花香打得他 从自行车上跌落,掉入花丛 刚吞了几口,身子却歪了,沉沉睡去 一梦到天明,次日在地心刨煤 被一夜花香泡透的身躯,却怎么也提不起气力 还不敢大口呼吸 怕鼻腔里残余的花香,加快挥发 ……尽管如此 ,悄然溢出的几缕春天 还是让整片煤田、整条巷道 皆缓缓地飘了几下、有点晕眩 稍不留神,没躲开一块脱落的矸石 干脆用手指蘸着含有少许花香的鲜血 在巷壁上写下几个字:春天来了 但我却看不见……。饥渴的煤体边轻声朗读 边飞快吃下这几笔狂草…… 什么也看不见了,但他仍不放心 用整个身躯狠命地在那儿蹭 (刊发于2010年第4期《扬子江诗刊》) 处女煤 我把地心深处的一块 未经开采的煤,叫处女煤 如今这块煤就用处女幽深 含蓄的黑眼球盯紧了我:它在这 光阴的背面,埋伏的那么深 像大地骨头中隐藏的病根 现在我必须把它采出 必须以一个男人的力量 去开垦这块处女的煤,拿起手镐 用力刨下我要让它从岩层不怀好意的 拥抱中脱落…… 一个恪守闺道一亿年的处女 待嫁的心情当然是迫切的 那就把它抬上地面,嫁给火吧 冬天的旷野上 从一场婚礼中蔓延出的 这片燎原的煤火 呼地一声就把太阳给烧没了 (刊发于2010年第4期《扬子江诗刊》) 受潮的闪电 槐花翻山越岭,成堆的蜜蜂 像解放的大军 ,一夜之间 占领平原乡镇,远方的山尖融化了半截 春天碧绿的纤指拨开了茂密的树丛 露出了湖蓝色的井架 运煤的卡车黑色甲壳虫般地,爬上盘山公路 临近几十个县的火电站都学着蜜蜂 嗡嗡地鸣叫着 吵醒一个矿工睡眠里的深刻 我吃过晚饭、背上矿灯、带上矿帽 穿上矿服,宛如一截受潮的闪电 悄悄地潜入地心 2007年1月 井架 头顶苍穹,背靠矿山 高耸入云的井架 隐藏到了那片湛蓝里 它用一双钢铁的巨掌 恣意地揉搓着晚秋寂寞的时光 脚踏地心的井架 在它的膝关节里有一种 年代久远的痛,它的每次深呼吸 都带来大片的煤潮和亘古的气息 它的脉搏已和大地的脉搏连成一体 大地的心跳就是它的心跳 在四周大树和禾苗的包围下 钢铁的井架已逐渐变绿 并悄然向高处拔节 高大的井架在远处斜阳之外 某个黄昏的小憩中 它突然梦见了自己倒映到 塌陷湖中的挺拔的倒影 2000年2月 通风机 对着巨大的井筒,它不停地吹气 强劲的气团沿深深的黑洞往 八百米以下走,地心大大小小的数百条巷道 充溢着它有力的深呼吸 众多的煤粉烟尘瓦斯 被风的大手推搡着剥去衣衫 赤条条地怒骂着,逃向阴暗的回风巷 矿山的通风机 它喘息的声音传遍辽阔的大平原 其中沾满了麦子的笑语、乡野的悲喜 人间的炎凉,直达在八百米地心 暮春时分,在井下的透过它深深浅浅的 呼吸,我看见了有穿稠衫的花香正在其中 跑来跑去的 听出了两个在花间偷情者欢快的喘息 劳作不息的通风机,也有生病之时 那天它偶感风寒,用生锈的肺吃力工作 井下十几个采掘工作面 数千个工人皆憋得汗流满面 像是被黑暗捏住了喉管 2003年11月 矿脉 雷暴乍起的时候 谁还吹嘘敢用浅蓝色的闪电 作为自己的纽扣 又到了上班时间 我带上矿灯 一寸寸退守至黑暗的地心,阳光从没光临 大雨更不会尾随而至 整片地心闷热潮湿 仿佛散发着整个安徽省的体温 每一块煤中都可能躲藏着 一个尖叫的生命 混淆着一块乌黑的雷霆 我割煤时分外小心,尽管如此 还有一些细碎的炭屑钻入我的肺管内 敢于抚摸雷霆的人 必管雷霆叫兄弟,在上井的时候 我的心里揣上了一座沉甸甸的矿脉 2006年3月 黑面包 车过淮河大桥 大河哗哗的水声 很亮的涂抹到人们的脸上 麦子深绿、民谣淡红 乘客们一身苍茫。大家欢呼雀跃 我的目光直钻河底 银鱼雪白、河沙浅黄、岩层灰白 我的目光象乌黑的泥鳅 一直向下钻着走 穿过明清的淤泥、唐宋的废墟 夏商的灰烬 穿过二叠纪、石炭纪 侏罗纪缩成的厚厚岩层 终于在负八百米地心的一处矿洞 收住它匆匆的脚步 牵扯住我冗长注视的是一群乌黑的汉子 象一群忙碌的工蚁 他们正举起牙齿一样锋利的大镐 扑向一块掩埋在地心的 巨型黑面包 2007年12月 (刊于2009年《诗歌月刊》第4期中旬刊) 照耀 上升到地面 浑身汗透面满乌黑,像一块直行的大炭 我更在许多炭块的后面,缓缓前行 毛绒绒的阳光扎的人肌肤发痒 我们每人都脱下上衣 用力抖下上面沾满的夜的粉末 迎面走来一群去参观井架的学生 美丽的女老师正说着矿山的重要 矿工的伟大,一见衣衫不整的我们 立刻关上了动听的喉咙,熄灭了语言中的火焰 只剩下面孔上缠绕的几缕,目瞪口呆的青烟 忽然从队伍中看见花枝招展的女儿 我忙着把头扭向清晨的另一侧 但她的动作更快、幅度更大 两束稚嫩的黑色闪电疾速地移向辽阔的秋空 但仅过了片刻,又勇敢地照回到我的脸上 “秋高气爽多么好 心的苹果在轻轻的摇““” 此时大声吟出叶赛宁诗句的是 天空飞过的一只鸟 2007年12月 (刊于2009年《诗歌月刊》第4期中旬刊) 下井 东风吹着麦苗 吹着村庄 东风扒开挂满乌云的树丛 乍现出远方井架湛蓝的脸 它不声不响地耸立着 仿佛一角裁下的碧天 淮河就在远方很响地流动着 滔滔不绝的淮河 把它粼粼不断的波纹 不停地投射到井架上,远远望去 仿佛淮河踩着高高的井架 一下子就从地面流到了天上 春天的傍晚,我背上矿灯 来到井口,仰望片刻 直到眼底蓄满的天空湛蓝 淮河苍黄、麦苗嫩绿 沉入到心底静湖中,然后才走上大罐 下陷至乌黑封闭的负八百米地心 2007年12月 (刊于2009年《诗歌月刊》第4期中旬刊) 黑煤上升 从负千百地心直至地表 无数钢铁的轮轴滚滚向前 一条绵亘的皮带、托着时间的远,岁月的黑 历史的深,向上开拔 时空是敛翅的一亿只乌鸦 重新起飞,一亿块上升的黑化石中必有 一块与我的心跳近似 还有一块与我的理想相同 听命于血脉中深埋的那道鲜血电流 皮带飞逝 ,轰隆隆的声音象雷霆开会 但屏住气息,仍能听清 它们内心深处的大梦与私语 口含焦虑的火焰 它们梦见了森林与泥沼 梦见了发电厂和炼钢炉 梦见了黑夜一米米缩小 冰川一片片焦糊,就这么梦下去 快抵达地面时 它们再也梦不见黑夜与冬天 2006年8月 河畔的矿山 一座高耸的井架 把许多人的梦想带入云间,井架不远处 一条大河不紧不慢地冲刷着平原的空旷 浑黄的波光,一片一片地在井架上闪动 黑色的煤浪 一阵一阵地从地壳之下涌出 载满黑色方言的火车爬上桥梁 装上固态火焰的船只火焰划响水面 河不醒不睡地流动,细碎的波纹 扩散到一天绚烂的朝霞里 河畔的矿山,像一个参禅的巨人 用目光里的坐标测量着天地间的洪荒 河畔的矿山,在寂寞的大平原上长醒 笔直的井筒如哲学家深邃的思想轨迹 深入地心 祖父、父亲从那儿潜进煤层,还有我······ 阵阵的豆花,带着隔世的芬芳从岸边吹过来 在墙角下裸露肌肤 吞食阳光的老矿工,怅然地望望高高的矸石山 他把逝去的、打了许多褶皱的旧时光 放在水杯中舒展开 咽下一口茶水 他满嘴回荡的都是阴消阳长的煤味 2001年7月 (刊发于2013年第2期《山东诗人》) 在淮河下采煤 在淮河下采煤 驾驭钢铁的综采机 切割浓郁的夜色 我灵魂一样轻盈的目光溢出乌黑的煤体 和厚厚的岩层,一直向上 直抵河心,溅起几朵冰凉、柔软的苍黄 在淮河下采煤 从狭小的巷道内,钢铁的支架中穿行 想象着阳春三月的一次郊游,柳絮癫狂,山泉烂漫 我的思绪中喂养的十几株桃花 张开粉嫩的香一点一点地挤开地心的黑暗 在淮河下采煤 大河把浩淼的波汶投射进了几百米深的地心 ——它正在厚厚的煤壁上 在我们乌黑的肌肤表面、粼粼不断地 书写着浑黄绵长的史诗、蝌蚪般地象形文字 一种跨越时空的传奇 2001年7月 (刊发于2013年第2期《山东诗人》) 春夜的矿山 春夜的矿山,和风吹响寂静 月牙把碎银洒满大街小巷 我西装革履的矿工兄弟们 来到明亮的厅堂 成为舞台上的主角 煤矿工人,烈火的兄弟们 跳起了如水的舞蹈 ,却游刃有余 飘逸的身态,牵动着浪漫的软风 吹散体内积压的黑色沉重 看!挖煤的大手拿起了小巧的话筒 听!粗犷的喉咙唱起了细腻的情歌 掌声雷动 ,彩灯闪烁 欢快的音乐洗去了一身的疲惫 生活的外延和内涵在厅堂顶上悬挂的彩灯中间 次次优美地扩散 于是 ,从矿山少女如水的双眸中 升起了座座棱角分明的苍山 在矿山少女涌动的心湖中 传出了爱情风帆划开岁月的水声 2001年7月 (刊发于2013年第2期《山东诗人》) 黑海.黑土地 时光的犁耙静止在松软的煤层中 广漠的黑土地,不再散发出新翻的气味 岁月的铁桨静止在凝固的岩浆中 辽阔的大黑海呀 不再呈现波澜万丈的辽阔 ·····斗转星移,石门打开 终于有一天,我像一粒种子 钻入黑土层中膨胀开,我像一片波涛 在黑海的内心雷鸣般喧响 2001年7月 (刊发于2013年第2期《山东诗人》) 井筒 像老家的木桶,埋在大地的肌体中 一幅宇宙无底的黑洞 两只钢铁的大罐是两把沉重的水舀 来回舀着地心的黑暗和旷古的感叹 桶壁上凿满的洞穴,通向大地的胸腹间 工蚁般的男人不分昼夜地,翻开乌黑的经幡 一页页撕下,打运到地面摊开, 交给远处秃头的群山,用四季风的语言默念 2001年7月(刊发于2013年第2期《山东诗人》) 写给瓦斯 又名沼气 学名甲烷 化学分子式CH4 能使人窒息死亡 可以剧烈燃烧 还兼有核弹般的爆炸力 它是瓦斯 是亿万年来大地强劲肠胃 无法消化干净的 史前动植物的不眠魂灵 隐藏于煤缝间 石缝内 它瞪大仇恨的双眼 盯紧侵入它内心的人 胸怀万丈叵测 时刻准备涌出或爆炸…… 假如它能够大声的读出我 在煤壁上 为它写的诗 肯定不会湮没这么多 无辜的生命 地心的蛙鸣 煤层中,像是发出了几声蛙鸣 放下镐仔细听,却不见任何动静 我捡起一块矸石,扔过去,一如扔向童年的柳塘 但却在乌黑的煤壁上弹了回来 并没有溅起一地的月光 继续采煤,一镐下去 似乎远处又有一声蛙鸣回荡…… (谁知道,这辽阔的地心,绵亘的煤层 到底湮没了多少亿万年前的生灵 天哪!没有阳光、碧波、翠柳 它们居然还能叫出声来) 不去理它,接着刨煤 只不过下镐时分外小心怕刨着什么东西 (谁敢说那一块煤中不含有几声旷古的蛙鸣) 漆黑的地心我一直在挖煤 远处有时会出几声深绿的鸣叫 几小时过后,我手中的硬镐 变成了柔软的柳条 活在伤口中 打眼、装药、放炮,躲炮的一瞬间 我要做的是,解下脖系的白毛巾擦汗 当汗水和疲倦,深入到柔软的之物中以后 当白毛巾变黑以后炮也响过了 煤壁轰然倒塌,地心深处 这条狭小的巷道又向前走了两米 呼呼的炮烟往回刮,用黑毛巾捂住口鼻 我探头望去,见前方狭小低矮的巷道 太像大地内心深处的一道伤口 活在长长的伤口中,像它的疼痛 我小心翼翼地弯腰前行 每一步都牵扯桌敏感的神经,我真实地感到了 大地的抽搐,地心摇摇晃晃 头顶哗哗到了几块碎石。我止住脚步 松开大地的神经 片刻,却发现栖身的这道伤口正悄悄愈合 狭小的巷道正悄悄收拢 黑色旗帜 叫吧,笑吧,跑吧 只要声音再高点,脚步再疯些,表情更 快乐些,兄弟们,在一分钟之内世界 就是你们的。一分钟之内,地球停止转动 田野生长沉寂,湖海泯灭歌声 一分钟之内,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宇宙中 只剩下三个漆黑的面孔,在独自萌发愉悦的枝条 六十秒以后再把世界还给别人吧 在黎明的井口刚浮出地表的,亦或是刚从一场事故中 逃生出的三个黑汉子,像三小块黑非洲 一次次不停地漂移,组合,分裂 ,追打出快乐的 地形图,三个疲惫的身躯迅速在晨风中展开 如三面破旧的黑色旗帜 抖动出危险和汗酸混合的味道 路人们纷纷掩鼻,侧身,躲开 这快乐彗星的撞击,总算还有一个没闪避开 为什么只是讴歌乌煤壁的乌黑 井架的威严,煤炭工业巨大的能量 却忘了其中暗含的人群,心头一热,我迎上前去 地心的梦 下井,忍受着大地内心深处万丈怒火 的焚烧,从它的肌体上剥下口粮 衣服,破房,剥下一个穷人所有的光荣与梦想 准备用这乌黑的煤 将我消瘦的日子,喂得白白胖胖 上窑,拿起生命的笔,蘸着体内捎上来的墨 写下乌黑的心跳,用生硬的土语朗读三遍 直到暗淡的身躯冒出 缕缕灵魂点燃黑煤产生的青烟 别人的梦在天上瓦蓝地高唱 我的梦在地心乌黑地摸爬 别人的歌在瞬间结果开花 我的诗喂了二十年还没长大 这就是我,过去的一个瘦弱落榜生 如今的一块着火黑化石 将来的一捧泛白煤渣灰 上升的梦 电车头飞驰向前,有三十张载满煤炭的矿车 三十座乌黑的光阴小城 在地心深处铺开亘古森林的墨韵 车上的炭块们,歪着脑袋窃窃私语 一张口便会溢出些酿造亿万年的酒香 巷道两旁没有被采下的煤层 望着这些欢呼雀跃的伙伴们满心地渴望 思想里洁白的雪花一个劲地往外刮 没有被采下的煤炭 梦见的是综掘机、液压支架、割煤机 煤炭工业史躯体里流淌的一条能量之河 被割下的煤炭,梦见的是牵着岁月根须飞奔的矿车 没有升上地面的煤块 梦见的是岩石里弥漫的绿意花香 升上地面的煤块梦见的是通红的炉膛 沸腾的钢水,时代的铜鞘内折叠起来的电力之剑 春天的清晨 这块煤田储量巨大的心事沿时空的隧道 从负八百米地心,踩着黑暗柔软的头颅 一点一点地往上爬 婚礼 主持这个仪式的 必须是一个老资格的矿工 参加婚礼的新郎必须是火焰 新娘必须是煤炭、,老矿工必须要面朝火焰 把一块用红绸子包裹的煤 举过头顶、念念有词 当他下跪时,坚硬的膝盖 必须要像两柄油锤 在大地上砸出另两眼浅浅的矿井 嘉宾离去 新郎把新娘抱上婚床 先用火焰颤抖的双手接去 新娘的的红嫁衣 然后再拥抱着她纵情地燃烧 当着烈火和黑玫瑰融为一体时 辽阔的天地就做了他们的洞房 装满煤块的贝壳 黑暗的大伞渐渐撑开,伞顶上镶满 暗淡的星辰。月亮是一个月牙形的缺口 从那里泻下独裁者惨淡经营的光 眼前的小煤矿寂静空荡 一排洋楼像是总结报告上了了的几笔 数缕服了雄性激素的山风从微合的 窗口,钻入到女浴池内 溅起了一片涂满洗发香波的惊叫 多少年了,有人一直在地心深处挖炭 有人一直在大地表面攉雪 有人一直在洋楼包间吃酒 不远处的淮河边,我捡起两只蚌壳 细细地凝望,它们苍老、斑驳 、易碎 其中灌满了宇宙中哲学的斑纹 隆隆轰响的撞击声传出,升上地面的矿车蜂拥而至 它们像另外一些贝壳 上面还装满了淘自地心的黑色慨叹 2011年9月 (刊发于2013年第2期《西部作家》) 约会 钢铁如林 煤壁耸立 狭长的工作面山一样地向下倾斜 黑暗之河携带着时间的落叶,哗哗地从头顶流过 这一切似曾相识,一个人坐在地心的空间 我在竭力地追忆,仿佛以一亿年以前我就光临过此地 仿佛我从没抵达过这里 天空中的乌云衔着鸟鸣压到了地面 眼见得狭小的工作面又低矮了两寸 顶上又掉落了两块矸石,身旁的井鼠 惊诧地望望我,四周充溢着煤体温热的呼吸 淡淡的沼气梦一样地漂移,时间已过去很久 在这乌黑的时空隧道中 我要等的那个家伙还没出现 他是个山顶洞人 还是从煤壁中飞出的一只始祖鸟 他是个刚站立起的猿猴 还是一群从长眠之处爬起的草原狼 或者他只是一缕似有似无的轻烟 从时空的上游,斜进我飘飘渺渺的身躯里 2011年9月 (刊发于2013年第2期《西部作家》) 独行 眼前一片漆黑,心里却起了秋霜 深夜子时,在这遥远的地质年代里 只此一人向前行走,没行上多长的一段 总是听见身后有莫名其妙的响动 似乎有人在用比尘埃还轻的脚步 悄悄跟踪 ……又走几步 感觉到巷顶还有人偷窥 冰锥般尖利的目光,直剜入身躯 忙举起矿灯,像举起自己怦怦乱跳的心脏 向头顶、身后一照,却只找到嗤嗤冷笑的黑暗 和谗岩煤块得意的脸 “已经封闭了亿年的地心 已经开采百年的老矿,什么怪事没有……” 我一边嘀咕,一边在这死过人的 老巷内、快走 “叭 叭”头顶和身后 又传来阴森的响动。几块长了眼睛的小矸石 擦着我体表的尖叫落下,快步行走 遍体上下抖落的惊骇 在瞬间变成了调零一地的史前落叶 2011年9月 (刊发于2013年第2期《西部作家》) 最后一班 汗珠已经在肌肤上建筑了若干个 流动的城阙。但手上的动作却丝毫没放松 被刨下的煤炭,即将把地心的黑暗和潮湿烘干 再让我干一会吧 这个明天即将退休的老工人 对身边的工友们 对周围的铁镐钢钎 对着绵延的煤壁次次央求 谁也不忍心拒绝他 地心的八小时很快就要过去 要上窑了,这个八百米深处的 资格最老的矿工早已泪流满面 他捧起地心的一块大炭 捧起一块小小的祖国,揣在怀里,让它的心跳 和自己胸腔中的那块冒着火焰的大炭 蹦成一片 上井的时候 他一步一叹,一步一回望,想在一瞬间 把过去四十年的路重新踩个九曲回肠 跟在后面的我们 只听见时间的鼓槌重重地敲了四十下 2011年9月 (刊发于2013年第2期《西部作家》) 头次下井 四周铁的围困中,我向往事的深处下沉 一声惊叫刚产生就黑暗被熄灭 快速陷落 我触摸到了时空的空旷与虚无 只有脚下的钢铁是最真实的 它使我在下坠的同时 感受到了一种上行的力量 我听见受到挤压的黑暗 象风一样轰鸣 我看到受到挤压的黑暗 像水一样层层匝开 是下沉也是上升 等到罐缓缓静止 钢铁的大门敞开 我们 便习以为常地深入到 一个久远的年代里淘金 1992年9月 (刊发于2013年第2期《西部作家》) 走在废弃的巷道中 走在废弃的巷道中 像走在岁月的断层里 我的目光里栖满了凭空倒下的古树 腐败干涸的泥沼 头顶上的巨石摇摇欲坠 如死神暗运的内力的拳头 脚下的积水臭浪翻涌 似黑暗眼窝释放出深不可测 走在废弃的巷道中 像走入大地的盲肠内 漆黑无光。在静极无声的狭小空间里 不停闪动的都是亮在黑暗体内 的电光 传过来传过去的都是激荡在 寂静深处的炸雷 陨石似的矸快在我头前脚后砸下 悲壮的念头一个接一个 在地心的长夜中怒放如花 走在废弃的巷道中,多久了 我全身的每个毛孔,都瞪大为雪亮的眼球 伸长为打开的双耳 感受着从时空的十个方向压过来 的动力。——狭小的巷道正悄悄收拢 走在废弃的巷道中 我把四周的黑暗与寂静 一滴一滴地吸收进骨头内 把体内的灯光与声音 一点一点地释放到空气中 2002年3月 (刊于2003年第11期阳光,获第五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 煤雕 狭小封闭的巷道内,扬起无数粉尘 这些细细的煤灰,宛如小小的刻刀 在你赤裸的肌肤上,精琢细雕 雕你的眼睛 雕你的肌肤,雕你的头颅 雕出一个蔑视黑暗的形状 雕出一个凛然向上的精气 雕出一个惊世骇俗的模样 把你斑破的前额 雕成一片横空出世的高原 把你突出的鼻梁,雕成一座兀立的孤峰 把你狭长的眉毛,雕成两片剑麻的尖叶 把你深邃的双目 雕成两样滚动黑白演讲的火山泉 把你粗粝的身躯 雕成一座巍然屹立的星球 工作面上,一座座煤雕移来移去 乌黑的煤粉四处游弋 闷热的气体大片用上 于是,你宽阔的前额成为源头 哗哗的大汗河流般涌下 在你全身的黑中 冲积出一片昏黄苍茫的大平原 1995年3月 (刊于2003年第11期阳光,获第五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 采煤时我想起雪 采煤时我想起雪 想起去年冬天的一次远游 ······飞舞的玉屑 盛开的红梅 ······顷刻间炎热的工作面上 吹来凉风阵阵 顶天立地的支柱棚架 忽如根根伸向高处的冰川 而被炸药崩塌的煤层 亦像一次触目惊心的雪崩,四处飞扬的煤屑 冰弹般溅到我裸露的肌肤上,炙出烙痕 采煤时我想起雪 想起雪白对黑暗的偎依 烈火和冰块的热恋 白与黑 冷与热 阴与阳 相融相依又相抵相抗 如同从八卦图中游出的两围神鱼 在黑暗的巷道内游弋嬉戏 采煤时我想起雪 是陷于何暗示对自身的一次提升,这思想中的强光 划开了地心的长夜 分裂之处 雪花飘的纷纷扬杨,这灵魂中的白 最终把大地内心深处的黑 引领出了沉沉的时空隧洞 1994年2月 (刊于2003年第11期阳光,获第五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 煤花 若干年前的一个春天 如梦如花的她,佩戴另一朵鲜嫩的花 下井去支援高产,但一次突发的事故 就轻易地揉碎她,像摧毁一朵地心仅有的花 此后,她美丽的生命 永远保持着青春的十九岁 在那年,我的头声啼哭 刚好划破笼罩在地表上的沉沉黑夜 二十年后又是春天 高大的我首次下井采煤 来到她青春永恒的那段巷道内 我一镐刨下去,煤堆大恸 乌黑的化石中忽地溅出 一朵奇丽的花,一只斑谰的黑蝶 就在此时,煤层中也发出了那声 已被湮没了二十年的细细的尖叫 流出了二十年前没来及 淌下的那一汪清泪 1994年2月 (刊于2003年第11期阳光,获第五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 命运中的两块石子 到了初恋时常来的山坡上 矿工吴乐义从悲伤的表情内 取出一张法院的传票 杂树丛中,一块伤痕累累的煤把脸上的痛苦 移向一朵移情别恋的昨日黄花 不住地哀求,叹息 尊严的海拔一寸寸地矮了下去 仿佛一片落叶就可以将其覆盖 风韵残存的女人 心跳一次溅起一堆脂粉的女人 脸上堆积了一寸多的轻蔑 还在继续增加厚度 ……他们的身影,他们的话语 冒出生命挥发时释放的缕缕青烟 散过祖国肌肤表面上、翠绿的山坡 还有许多和两人神情酷似的石子 呆立在同样的命运里 庆幸 躲炮小憩时 他小心翼翼地弹落身上的煤灰 露出了干净的窑衣 指着那上面沾满初生婴儿的啼哭给我看: “终于做了爸爸!”他幸福又幸福的表情 恰似充足了能量的电钻 旋地刺透了地心亘古的黑暗 炮烟散尽,他又上前低头扒煤 却不曾想顶上“哗啦”一下 后面的事勿须多言 反正这在井下司空见惯 正呆呆发愣间 身旁的煤壁扳着哲学家的黑脸 冷冷地开口了:“辽阔的世界上, 当一个人嫩芽般地萌出之时 另一个必须得春雪般得化干净。” 没有搭理,心里一半悲怆 一半庆幸:还好此事已经错过了昨天 时间的黑炸药 有些被泯没已久的东西 容易在一瞬间迸发 比如说地雷、比如说瓦斯 比如说大地内心的万丈怒火 而岁月总喜欢掩埋一些东西 比如说记忆、比如说尘沙 比如说大地英年早逝的梦想 因此、许多森林在青春年少时 就让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 埋葬在封闭的地心深处,它们不断地分化、挤压 收缩生存空间。直至······ 一亿年以后,再打开地球,开始阅读 便会发现:从太古代到古生代 从侏罗纪到石炭纪 从世间的肌肤到岁月的骨髓 到处是被掩埋的黑色炸药,在静等怒火的引爆 像是有一个抱恨者,把无边的敌意 刻骨的仇恨 播种进了仇人可能出没的所有的空间里 最亮的光明 煤块体内黑暗的器官一定是由 最亮的光明所构成,不信你用思想将它点燃 它是闪电的婴儿,月亮的根须 深邃时空海底里道德的准绳 地球童年悲剧和谎言的青涩结晶 在采煤时必须默默无声 拉紧身体的弦,射出劳动的箭 头颅内的海啸,心房内的金矿 被高高抡起的铁镐,划出远海的光 黑暗中的织女星蓦地一现,煤流滚滚, 地心的疼痛喊出来,就是暴怒的雷管 时空里最深的谜底就埋在负八百米地心 一群群半裸的莽汉撕扯下地心的黑暗 做长袍、做短褂、做糊口的黑米白面 井口刮来一阵冬天的微风。吹灭了矿工呼吸上 点燃的危险灯盏 2008年5月 散步 老狗领路,竹杖搀扶 才向前走上几十米,全身已被回忆的汗水煮透 他抬头看看辽阔的乡野 ——如此漫长的路,用尽躯体里余下的生命卷尺 是否能丈量的完。童年的村庄,青年的流浪 中年的矿井,他一边用拐杖敲打大地鼓面上的低音区 一边侧耳倾听,从地心深处传回的 雷霆撞击炸药的巨响 前方,一推垫路的矸石,躯体表面涂满 危险打的蜡,他放慢脚步小心翼翼地踏上去 天知道那里面会不会,隐藏着另一支瞎火 的雷管。他不敢再用力敲打,仇恨的内分泌当量惊人 一刨下去,可能还会发生一次爆炸 再将自己仅存的右腿崩断 他心有余悸地摸了下左腿的残部 里面依旧隐痛阵阵,像一座倒塌了一半的 采煤工作面,一节被工业文明野蛮截断的黑树干 几十年依旧没再发芽长叶,他忿忿不平地望望远方 那只老狗正恼怒地对着夕阳里通红的矿藏狂吠 2008年5月 八月十五 八月十五,蟋蟀的叫声砌成一堵乡野居士的 篱笆墙。翻墙而入的是菊花、是夜露 是田野上没来及入仓的稻香 大地打开双核处理器下载月光,淮河平原 多么辽阔。地表上长庄稼,地心里长煤炭 爸爸拿起叉扬到家后整理稻草的笑语 妈妈挥动苕帚去清理老杨树的阴影 我趴在高高的树梢上用目光 一点一点地荡开村庄与煤矿之间黑暗的海平面 下井的哥哥还没回来 秋风和黄叶关于祸福的唯物主义辩论,还在继续 香案前奶奶断断续续的念叨声 像一辆破旧的手扶拖拉机,载着哥哥的名字 在门前的小路上颠簸出一地悲悯的月光
田力,爱诗写诗的福报——民间诗人走进《鲁豫有约》 |
|
Copy all rights reserved for www.hnpictures.com
淮南图片网 版权所有
地址:淮南市阳光国际城南区7号楼507室
备案号:皖ICP备15022074号-2
电话:13505548206、18949682288
邮箱:1147587489@qq.com
网站特聘律师:胡蓉
技术支持:淮南讯网